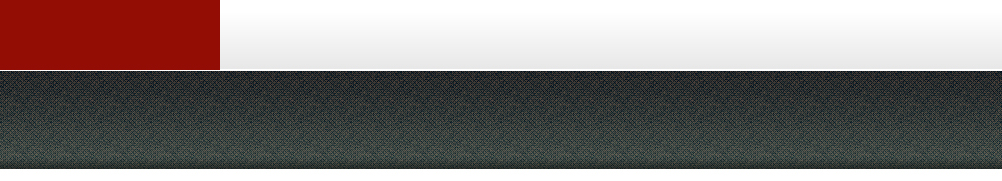早就听说过北大荒“棒打狍子瓢舀鱼”,对此一直是半信半疑,哪有那么多的狍子等着你打?这只不过是一种夸张的渲染罢了。看了杜崇山讲的故事,知道“瓢舀鱼”的事儿是靠谱的。因为人家下乡的地方就在兴凯湖的小黑河,小黑河鱼多,多到啥程度?老娘们儿在家做晚饭,老爷们儿下班回家,拿了网出去了。家里的饭还没焖好,人家拎着鱼回来了,而且那鱼都是收拾好的,直接下锅。
看着眼皮底下的鱼,知青们干着急。为什么?没有渔网。当地没有卖渔网的,打鱼的网全是自己织的。杜崇山就想自己也织个渔网,这样既能玩乐又有鱼吃,多美的事儿。他是连队材料保管员,人头熟,就找了会织网的师傅请教一番,什么底兜、网眼、织扣、网铰子,以及织法。问明白了,就托天津知青买回一斤尼龙线,照葫芦画瓢,竟也织了一张旋网。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的知青哥们儿们以极大的耐心盼来了试网,不知是网好还是鱼多,反正是上鱼了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你方唱罢我登场,大家轮流拿网捞鱼,杜崇山见天看不见自己织的网。今天不见了,明天又挂在吊环架子上了,后天又没了。但是休息日的渔网,必是归杜崇山使用。到时约上好友几人,带了白酒馒头大料辣椒脸盆镰刀,顺着河边边走边撒网。打够一盆了,土块儿垒灶,镰刀割柴,脸盆烹鱼,放了大料辣椒,满了白酒。众兄弟席地围坐,撅了苇子秆蒿子秆擦吧擦吧就是筷子,轮流端起搪瓷盆喝酒,大口吃着原味河鱼,吹牛侃大山,煮鱼论英雄,好不惬意。
渔网给知青们带来快乐,最应该感谢的一个人就是邢子山。邢子山小名小山子,他和杜崇山光腚时就在一起,货真价实的发小。看见杜崇山织渔网,他主动上手帮忙。小山子手巧,拆了水果筐上的竹篾做成梭子梭板,刻制了铰模子铸了一百多个网铰子,他织渔网又快又好,后期制作中拴底纲绑网铰子上桐油,都是他一个人干的。心灵手巧热心肠的小山子既是快乐的制造者,也是快乐的参与者。他和兄弟们郊游于小黑河边,在草地上追逐撒野,在花丛中闭目养神,在鱼锅旁把酒狂聊,一起享受着渔网带给他们的欢愉时光。那一刻,他们忘了辛苦劳累,忘了亲人家乡,忘了明天和梦想……。
然而杜崇山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,都会夹杂在美好和难过之间,因为小山子在一次意外中英年早逝了。在他心里,小山子和渔网已经成了一个共同的故事,所以他以网祭人,写下这篇文章。
人生大抵如此。站在起点时,大家比肩而拥,一路向前。走着走着,就有那掉队的。或分手,或失联,或逝去,离终点越近,能见到的能听到的就越少。唯有心底的记忆没有磨灭,时常会想起曾经在一起的同事同学朋友,想起大家在一起经历过的日子和故事,想起共同的欢乐和悲伤,歌唱和哭泣。今天,我们50后的大多数人还在走着,不同的是,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动和盲从,更多的是自信和从容,毕竟我们已经走了那么久。
兴凯湖农场四面环水,水资源丰富,水多鱼多。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时候,鱼是多的不得了,说句不是吹牛皮的大实话,马蹄坑有鱼是唻玄,基本上有水坑的地方就有鱼是绝对的。值班二连紧靠小黑河,鱼就更多的了不得。小黑河连着松阿察河,通到乌苏里江,然后汇合松花江、黑龙江流向大海。鱼的来源广阔,水稻田里圈鱼、排水沟里抓鱼,手到擒来,那是取之不尽,食之不竭。
靠着这方福地,连里的住户们家家都有网,捕鱼吃鱼就别说有多方便了。可以这么说,中午下班,妻子在家做饭,丈夫出门到河边打鱼,丈夫拎着收拾利索好的鱼回来了,妻子的主食还没有出锅呐。这一点儿不胡说,真的就这么快。
守着这么好的鱼资源,可知青们只能干看着,二十几个青年宿舍里竟没有一片渔网。很多人都渴望有个网,这样就能多一个玩的工具,打来鱼还可以顺便改善一下生活。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,有乐为什么不为呢。后来弄明白了有乐不为的原因,是因为没有地方买网,而知青们又没有人自己会织鱼网。
一定要有个自己的渔网,这个想法在我心里是牵肠挂肚,总惦记着这个事。后来一营营部撤销,从营部调来一些老同志,我那时做连队材料保管员,因工作接触多,很快和这些老职工混熟了,谈及渔网的事,他们说织网好学,知道一些基本东西你自己就会干。油料保管员唐荣师傅还拿来一张网打开告诉我,多少底兜就起多少眼的头,剩下就是几行隔几个眼加一个眼,到什么时候如何织都有一定章法,学会织扣就可以干了。见他们说的如此简单容易,我那颗对织渔网渴望的心,蠢蠢欲动、跃跃欲试、且信心十足。
天下没有学不会的手艺,况且现成的师傅在身边,不会时可以随时请教,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个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。放春节探亲假了,我托回天津探亲的知青孟庆新战友,帮助买了一斤适合的尼龙线,做了一些必要的物资准备,就开始了自己动手织渔网的工程。
邢子山跟我从小在哈尔滨住一个居民院,是一起长大的光腚娃娃,小时候他妈妈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山子,我们一天上山下乡离家,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兴凯湖农场。刚来时,我在岗下十二连,山子在南岗上十四连。1969年夏天,我先他后,间隔两个月都调到值班一连,共同经历了两年备战军训的准军事生活。1971年5月,我们同时被“掺沙子”调到值班二连。邢子山从小心灵手巧,还会一些木工活,得知我要自己织渔网,他就过来伸手入伙,和我一起织渔网。山子从装水果的筐上拆下竹板,自己制作了梭子、梭板,我们起了一个30个底兜的开头,就正式开工了。除了吃饭、上班、睡觉时间,其他业余时间我们两个人轮流操作。山子比我手巧,织得比我快,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就请教师傅们。利用我织网的时间,山子刻好了铰模子,我们利用废旧铅皮和从哈尔滨背回来的铅块,铸出了120个网铰子。后期拴底纲,绑网铰子,桐油油网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干的活,都是山子一个人完成了。旋网终于织成,并用熬熟的桐油搓透,挂在宿舍门前吊环架上晾晒,等待桐油干透。大家纷纷来观看我们俩人的杰作,从此有渔网了,不用看着老职工打鱼眼馋,自己也有得玩儿了,同志们个个喜上眉梢,自然是夸赞声不断了……在集体宿舍,这可是蝎子粑粑——独一份啊。
大家以极大的耐心,终于等到网干透了,山子带着一群人,拿着网去河边试网,撒网也是一门学问,看着人家撒出去网开溜圆,潇洒飘逸,不用心根本撒不开,一个团团睡在水里,“咕咚”激起一股水花。在师傅的指导下,先在陆地撒,一下比一下像样,再到河里实践,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有模有样了。
从此,这张网就成了夏天里宿舍弟兄们最好的玩意,搭在吊环架上,很少有闲着的时候,中午晚上,不是这个拿走,就是那个借去。我和山子经常看不到网哪里去了,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挂在吊环架上了,与原来不同的是网上多了一些窟窿。为避免窟窿更大,我们赶快把窟窿补好,可一转眼渔网又不见了。都是住集体宿舍、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,没有那么多的说道与客套,山子和我也甘愿做这个穿梭结洞的补网人。
但是休息日这网必须归我们主人家使用,那可是最轻松惬意的时候,打鱼兼野游,现在想起来,那滋味可说是优哉、游哉、悠哉、友哉啊!
星期日吃过早饭,一帮要好的弟兄开始行动,拿上买好的馒头,到小卖店买上几斤酒,带上平时备好的大料辣椒等,不能忘了镰刀和大脸盆。拎着渔网沿河而上或而下,边走边撒网,有人打鱼,有人摘鱼,有人收拾鱼,有人打零杂,还有机动拾遗补缺。每个人分工明确,各司其职,配合默契,井井有条,打满一盆鱼,停止捕鱼作业,开始进行下一个科目,找一个背风的去处,埋锅烹鱼。从地边拖拉机抠泥形成的土块中拿来三块做锅灶,架起鱼盆,放满水,调料就是几个八角、一大把辣椒、适量食盐,如果运气好附近有鲅蒿,烹出的味道就更好些,手掰刀割附近枯枝荒草当燃料,点火烹制,天然原生态,河水炖河鱼。
渔网撒开晾在绿草上,除一人看火添柴,一众人躺在花草之中,眼望着蔚蓝色的天空,吸着劣等纸烟,闻着随风飘来的阵阵鱼香,谈天论地,吹牛侃山,有时候为了一个事情展开擂台赛,一人舌战群雄。鱼熟了,烹鱼者一声吆喝,开啜。众人各自从花草中跃起,撅根蒿子杆、苇子杆刮巴刮巴当筷子,鱼盆端在平地的草上,大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,两个塘瓷饭盆倒上白酒,兄弟们轮流推杯换盏,传来递去。喝着辛辣的老白干,嚼着鲜香四溢、原汁原味的河水炖河鱼,心里美呀,这可是在城里吃不到的纯天然美味佳肴。二两酒下肚,开始了鲜鱼烈酒论英雄,牛皮吹的更响,侃山唻得更悬,直至面红耳热、酒足饭饱,余兴犹存地收拾家伙班师回营。
夏天的休息日,我们经常这样度过,一张小渔网,给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弟兄们带来了不少乐趣,让宿舍里的哥儿们,在紧张的辛勤劳作之余,享受了些许的安宁与惬意,暂时忘却了工作的艰辛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。
四十多年过去了,每每想起这段陈年趣事,心里就是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。兴凯湖农场——我们的第二故乡,故乡的小黑河,养育了河边的值班二连人,而鱼和网,就是大自然对小黑河人的恩赐。
十几年前,渔网的主要编织人、我的发小——山子,因一场意外英年仙逝,过早离开了我们,留下这小黑河畔渔网和鱼的往事,让我常常把他怀念。
杜崇山,哈尔滨知青,1968年10月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(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3团),在那里工作生活了近42年,曾任兴凯湖农场党委书记、场长,社区管理委员会主任。直至2009年11月离开兴凯湖农场。